
这份名单秘而不宣,只在有限范围内使用。公安机关会从它上面找违法线索,连银行也格外关注它上面的名字。
名单上的每个人,都是法庭的常客。比如马维,明处,他是安徽的一家水果店店主;暗中,他在浙江以放贷为业。9年前,跟着老乡来到浙江省玉环市以后,他开始向人放款,欠债不还的,会被他诉上法庭。玉环市人民法院受理的与他有关的案子越积越多。
直到,,他上了这份“黑名单”。2018年2月24日,玉环法院出台了《关于建立“职业放贷人名录”的若干实施意见》。该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王再桑对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介绍,他们“第一个吃了螃蟹”,当时在国内属于首创。提出“职业放贷人”名录并落成制度出台的,玉环法院是头一家。
10月28日,马维再一次来到玉环法院,签了一份文书。他自愿放弃本人债权,涉及2015年至2017年间的18起民间借贷案,标的额从1万元出头到11万元不等,总额将近60万元,一笔勾销。
这份名单上的人,申请撤诉的案件迄今有151件。
“这些人明显紧张了。”玉环法院立案庭庭长陈巧峰说。
据法官们观察,这些人撤诉时,明明是放弃对别人追债,字签完了,松了一口气的反而是他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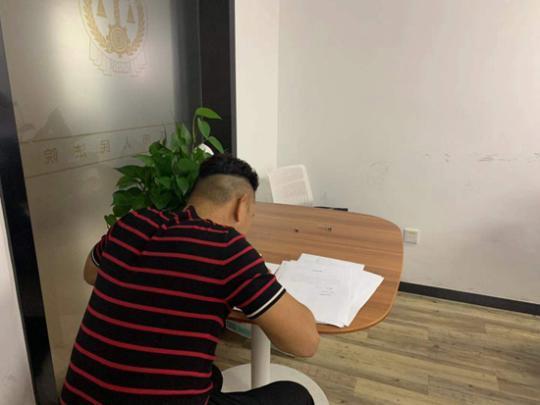
一位职业放贷人在浙江玉环法院签署18份自愿放弃本人债权的结案证明。玉环法院供图
隐藏的暴利
截至目前,玉环法院已统计出“职业放贷人”名录8期共694人,最多的一期超过百人。
马维登上这份名单的原因是,根据玉环法院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前三年数据统计,以他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累计达38件。2014年至2017年间,以他等7人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高达237件。
此前,这些人以债务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不同案件中。有经验的法官能够辨别出他们:他们与被告之间素不相识,他们总能拿出借条,而且总能用那些借条或者别的手段,隐藏纸面之外的高利率。
作为一名从业20余年的法官,陈巧峰有一种敏锐的直觉。听了情况后,他能辨别出谁是“吃职业饭的”:钱款中总有部分以现金方式交易而不会留下银行记录;把钱借给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;有些放贷人明面上就很直白,放贷会直截了当跟对方讲明,放款并不足额,因为自己会预先扣下一部分。
比如,一位放贷人专门借钱给在校大学生,约好借出1万元,却只给对方7000元。利率“巧妙”降低了。仅在2018年前3个月,此人就涉及16个借贷案件。
这位法官不止一次看到,“职业放贷人”喜欢把手伸向“最基层”。比如,借给一位农村妇女一两万元,口头约定每3天支付本息一次,直至付清。因为数额较小,借款人就算还不上,一般也能找亲友凑上,这种放贷属于“低风险”、高利率。
一些债务搅到了夫妻共同的债务认定中,一位男子借了9000元,一直没有归还,他和妻子一起成了被告。
隐藏在欠款背后的事实是:那位放贷人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高达32件,他专门瞄准短期内需要用钱的人,开出高额利息。借款的男子有赌博习惯,3个月内借钱8笔,总额21万元,而他妻子的银行账户里资金充裕。
“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往来。”陈巧峰说,这些原告经常借贷给他人,并收取高额利息,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行为。
由于制造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,玉环市的民间资本一直处于较为活跃的状态。由此带来的是该院民间借贷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。2017年,该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3629件,占民事收案总数近三成。
陈巧峰办过一个案件,一个水利局干部借了一笔钱,后来逃走了。放贷人起诉到法院,要求担保人承担这笔欠款。按照放贷人的说法,对方只付过3个月的利息。按照经验,法官判断,向陌生人出借钱款,要么是收取了高额利息,要么就是已拿到部分还款,只付了3个月利息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。
此类案件中,不少被告没什么法律意识,借条上的出借人一栏为空白,也稀里糊涂地签了字。出借人空白是一个典型的“套路”,有的人直到庭审对着一叠汇款凭证时才突然傻眼,自己的还款对象是另一个人,而不是原告。
“法官毕竟不是公安干警,不能主动以职权侦查,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,处于弱势的被告也很难拿出有力证据,即使法院有权调取,事后再采集也为时已晚,就像现金交易根本找不到凭据。”陈巧峰反问,“你说怎么查得清楚?”
还有一些案件,即便被告已支付利息或本金,因为是现金交易,被告拿不出凭证,原告予以否认。结果是,原告又通过诉讼让对方连本带息再承担一回。
有时候,陈巧峰也觉得自己挺“拧巴”:看着出借人“睁眼说瞎话”,自己“心里跟明镜似的”,可面对被告也只能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。囿于证据规则的规定,法官只能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对案件事实作出原告胜诉的判断,即使可能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并不一致。
“这类官司太难打了”
压力不仅在于判决,还在执行。这些年,陈巧峰总能听到一些来自民间的呼声。执行干警反映,案件执行时,赶到借款人的所在地,迎接他们的是对方“劈头盖脸”的一顿埋怨,当地人气得大喊,“法院还帮着放高利贷的人出气哩”。
王再桑做过几年的执行局局长。他发现,这些放贷人曾闹出不少乱子——把借款人的门窗砸碎,或者在墙壁喷上“天理不容”字样。“引起的民愤非常大,非常大。”
如果放贷人前几天刚来追债,法院再来强制查封借款人财产,看上去法院就成了放贷人的“保护伞”,给人“一条龙服务”的嫌疑。
面对这些,陈巧峰能做的,也只有当庭苦口婆心地劝说。不过,多数时候没什么用,一次次向原告代理律师阐明实事求是,换来的是对方的信誓旦旦,“当事人就是这么说的呀”。
“与其说是对判决结果的痛,不如说是对这些出借人嚣张气焰无可奈何的痛。”他叹气。
王再桑说,因为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,法院没有权力拒绝他们以正常的民间借贷起诉,必须按照流程走。并且在裁判方面,也没有一个规范此类行为的统一裁判指引。
一个人放了100笔借款出去,如果遇到违约,他可以去法院起诉100次。“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约束机制。”王再桑说。
直到去年,事情才发生陡转。
当地一名护士蔡涵被诉至法院。她30岁出头,一次职称考试中,她一门不及格。因相信有人能在电脑终端篡改成绩,她联系上对方。
对方向其提出要9万元办事费。为了拿出这笔钱,蔡涵经人介绍向虞立借款。虞立与罗凯洋是好友,经常将钱放在罗凯洋处周转,因此借给蔡涵的钱实际上由罗凯洋交付。
不久后,虞立作为原告、罗凯洋作为第三人,向玉环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蔡涵偿还借条上所写的共22万元借款,可蔡涵说,实际交付金额只有12.8万元。
“这类官司太难打了。”蔡涵的代理律师对记者说,他代理过不少类似的民间借贷案件,可被告证据相对比较完整的,想来想去也没几个。原告有借条,双方对交付方式没异议,争议只在交付金额,原告显然在证据上占优势。
案子交到了陈巧峰手中。按照原告出示的借条,其中的数额几乎比实际交付款项翻了一番,他不信这个关键性的证据。查证得到的信息也印证了他的判断——通过汇款凭证、支付宝电子回单、微信交易记录等,陈巧峰发现,罗凯洋的转账记录就是12.8万元。
可罗凯洋在法庭上的描述却“有鼻子有眼儿”。他称,当时自己刚买车回来,身上有9万多元现金。去医院见蔡涵时,他把5万元放进羽绒服里,剩下的三四万元塞进手提包。晚上8点多,他来到蔡涵所在的科室,先是签了借条,之后把现金给了她,剩下的12.8万元在走廊里通过手机转了过去。
类似这样的说辞,陈巧峰并不陌生。比大多数被告幸运的是,蔡涵还有一份来自医院的监控录像。录像中,罗凯洋仅拎一个手包就进了医院,其中放入约4万元现金的可能性很小;如果约定给付现金,大可将9万多元放在袋子里拎去,分别放在身上、包里不合常理。
进一步调取记录,陈巧峰又有了新发现:近几年来,罗凯洋和虞立在该院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分别达到26件和13件,都是玉环法院的“老面孔”了。其中,罗凯洋仅与该案被告蔡涵相关的民间借贷案件就有3件,立案标的金额40余万元。
罗凯洋与蔡涵之间的另一笔借款显示,罗凯洋曾汇给蔡涵2.4万元,一个月后蔡涵支付3万元,多出的6000元是按借款的惯例所预收的利息款。
此前,罗凯洋在该法院涉诉的26件案件,均是委托同一律师出庭,均使用格式统一的借条,借款普遍由其他人提供担保……这些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结论——罗凯洋是一名“职业放贷人”。
法庭最终认定,蔡涵收到的实际款项就是12.8万元,远小于原告主张金额。后来,虞立不服提起上诉,二审仍维持原判。
陈巧峰也终于“强势”起来。因与蔡涵的数笔借款中,罗凯洋采取多打本金虚增借款以掩盖高利放贷事实,多次要求蔡涵出具虚高本金的借条,在蔡涵已按照实际交付的金额将借款偿还完毕之后,仍然就借条中虚高部分的本金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,已涉嫌“套路贷”刑事犯罪。
审理了这起民事案件后,玉环法院向玉环市公安局移送了这个“套路贷”刑事案件线索。
陈巧峰告诉记者,这是玉环法院首例移送公安的“套路贷”案件。
也是从这次判决开始,玉环法院第一次在判决中提出“职业放贷人”的概念。陈巧峰在审理中发现,此前他的同事早已与罗凯洋打过交道。但是,面对“职业放贷人”,法院对这类案件没有有机地整合,因此,每一次接手新案件的法官难以作出更贴近事实的判决。
借着这个机会,玉环法院对近3年间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统计,结果是,同一原告5-9次起诉的有267人,10-14次起诉的有83人,15次以上起诉的有95人,最多的起诉次数甚至达到101次。
王再桑说:“放贷的现象早些年就有,但这几年,其职业化的特征更加突出了。”他说,一些年轻人没正经工作,靠来回借款折腾来出借资金,一旦对方“跑路”,钱收不回来,就会引起连锁反应。“对借款人和出借人来说,是双输。”
“或构成非法经营罪”
这些年,王再桑目睹民间借贷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:高利贷现象突出,超过银行利率好几倍;放贷人有组织成规模,借贷流程套路化,连还款的债务催收模式都很清晰。这些借贷的用途往往并非正常生产生活需要,有时是一些高风险经营,或是高负债情形下的“拆东墙补西墙”,甚至会掺杂一些赌博或,。
他坐不住了。在他牵头调研的基础上,玉环法院去年出台了那份意见,随后统计出第一期“职业放贷人”名录。
纳入“职业放贷人”名录的标准是:至统计截止时间的3年内,同一或关联原告在该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起以上民间借贷诉讼(含诉前调解),或同一年度内涉及10起以上民间借贷诉讼的原告。
这份名单,每个季度都会更新一次。因为是滚动的,不少“职业放贷人”长期挂在上面。
这份名单不对外公开,但在法院内部是共享的。王再桑解释,从案件受理到审判再到执行,有了这个名单依托,法官对“职业放贷人”利用诉讼程序实现“非法利益合法化”进行了严格规制,会有相应不利的认定。
比如,如果被告抗辩原告存在“当头抽利”或“隐性高利”“利息转汇他人”等高利贷情形的,法院会一律比对原告其他案件事实认定或被告抗辩,并作为争议事实认定的重要考量因素。法院还会从严查处冒充他人提起诉讼、篡改伪造证据、签署保证书后虚假陈述、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民事诉讼行为。
王再桑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,“黑名单”上的“职业放贷人”,即使是胜诉,因放贷而收回的利息部分,还要依法征收20%左右的个人所得税,这笔税收会被依法划转到税务机关指定账户。
这个举措令职业放贷人感受到“切肤之痛”。玉环市从2018年5月开始施行。今年6月30日,浙江省,人民法院与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也研究制定了类似措施。
按照王再桑的统计,截至今年10月,16个案件共10人已被征税10.6万元,其中,一笔征税额近6万元。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,当地民间借贷执行案件同比下降46.8%。
在玉环市,累计标的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原告,其名字就不只存在在法院的“黑名单”里,还会被抄送至玉环市委政法委、玉环市人民银行、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。
“这类人如果向银行融资,需要以高风险情况对待;如果要创办公司,相关部门也会盯着监管。”王再桑说。
当地公安部门也时不时会通过这份名录,调出相应案件的判决书,查找违法犯罪线索。
制定“职业放贷人”名单之前,法院也曾有过顾虑——把这些人“标签化”,会不会对其名誉造成影响?毕竟没有法律指引,一个基层法院用这种方式界定是否合适?王再桑说:“但总得有个突破。”
出乎他的意料,一些上了名单的人自己找上门来了。通过律师或其他渠道,作为申请执行人,刘勇找到了执行法官钟永长。这位“黑名单”里的人,3年来在法院累积了29个案子,总金额50.28万元。他主动撤销了所有案子,以及还未被执行的22万元债权。他还联系了好友马维,劝对方一起撤案。那位专向大学生放贷的人,同时放弃了13个案件的债权。
陈巧峰目睹了不少“职业放贷人”的背影。他介绍,民间借贷案件收案数直线下降,原有案件的许多原告也纷纷撤诉。在当地,已基本没有律师愿为此类案件代理而承担可能存在的虚假诉讼风险。
玉环法院统计,今年1-10月,该院的民间借贷收案数同比下降了19.22%。
2018年4月23日,玉环市委政法委牵头,联合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7家单位,共同出台了《关于建立协同整治“职业放贷”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。
今年10月21日,,人民法院、,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正式施行,该规定明确,无资质的放贷人以超过36%的实际年利率放贷,2年内10次放贷以上“或构成非法经营罪”。
浙江省台州市的9个法院也已推广“职业放贷人名录”制度,如今,外地更多的法院也正在进行尝试和探索。
在玉环,法官们还记得,第一份“职业放贷人”名单出炉后的前5天,名单上的那些人,向法院申请撤诉的案件就有25件。
(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)
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










